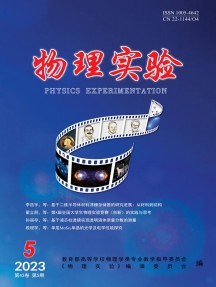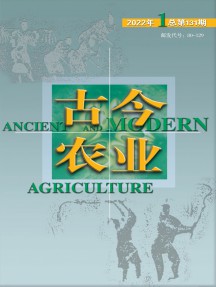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chǔ)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間:2023-09-25 11:24:03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chǔ),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關(guān)鍵詞:馬基雅維利《君主論》 政治思想 影響和評價
馬基雅維利是西方近代政治學(xué)的奠基者,他的政治思想對政治學(xu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貢獻(xiàn):一方面他使政治與道德分離,政治不再是道德的附庸,開創(chuàng)了近代政治學(xué)的新紀(jì)元;另一方面,他使政治與宗教分離,政治不再束縛于神學(xué),而是從人、人性出發(fā)研究政治,近代政治學(xué)終于誕生。馬基雅維利一生著作頗多:《君主論》(1513),《論提圖斯.李維的前十卷》(1513),《用兵之道》(1521),《佛羅侖薩史》(1525)等等。
一、《君主論》
馬基雅維利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xué)――基于人性惡觀念之上的“權(quán)力哲學(xué)”。近代政治思想也正是在這個邏輯起點(diǎn)上展開了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在《君主論》這本書中,作者集中論述了其君主專制理論和君子統(tǒng)治術(shù)思想。
全書共有二十六章。其內(nèi)容基本上涵蓋了君力的形式、來源、管理和如何維持。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作者論述了君主國的性質(zhì)、種類以及獲得它們的方式。君主國包括:世襲的、混合的、市民的、教會的這四種,獲取君主國的方式包括:通過自己的軍隊(duì)和能力獲得、依靠他人的軍隊(duì)和依靠幸運(yùn)獲得、通過犯罪方式獲得。作者對君主國權(quán)力的來源進(jìn)行了深入分析,教讀者如何對當(dāng)時的形勢和權(quán)力分布進(jìn)行分析,并協(xié)調(diào)這些力量。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至十四章),作者論述了軍隊(duì)的種類和君主在軍事方面的責(zé)任。軍隊(duì)包括:援軍、混合軍、雇傭軍和自己的軍隊(duì)。從政治的角度講,任何軍隊(duì)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團(tuán),軍隊(duì)為自己實(shí)質(zhì)領(lǐng)導(dǎo)服務(wù)。所以,要讓軍隊(duì)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軍隊(duì)。在軍事方面,英明的君主應(yīng)該整頓軍隊(duì)訓(xùn)練士卒,思考戰(zhàn)略,博覽歷史,分析成敗。第三部分(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作者論述了君主應(yīng)以國家利益和人民立場為重。就國內(nèi)而言,明智的君主應(yīng)當(dāng)急民眾之所急,賞罰分明;就君臣而言,親賢臣,遠(yuǎn)小人;就國際而言,敵友分明,立場堅(jiān)定。第四部分(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作者從歷史的角度,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其過去、現(xiàn)在的國家和政治,并勸告當(dāng)時君主爭取意大利的解放。
二、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所闡述的政治思想
首先,人性惡。馬基雅維利從經(jīng)驗(yàn)論的觀點(diǎn)出發(fā),認(rèn)為人性雖然有善的一面,更有惡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性質(zhì)而言是惡的。從古到今,所有人都無一例外的受到利欲的驅(qū)使,所有人都毫無道德可言。事實(shí)上,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從柏拉圖到中世紀(jì),大多數(shù)的政治家都本著政治道德化,人性本善的觀念,用道德掩蓋政治,使政治從屬于道德。到了中世紀(jì),神學(xué)政治論更使政治淪為神學(xué)的工具。而馬基雅維利的性惡論,一反常態(tài),標(biāo)新立異。馬基雅維利所認(rèn)為的人性惡,其主要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然屬性,這種惡,直接體現(xiàn)在世俗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爭斗與沖突。
其次,權(quán)力政治觀。權(quán)力是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所謂的權(quán)力就是實(shí)力,也就是《君主論》中經(jīng)常提到的“能力”。馬基雅維利斷言,任何一個擁有權(quán)力的人都想擁有更大的權(quán)力,國家一經(jīng)建立就面臨著對內(nèi)部敵人的鎮(zhèn)壓和與臨近諸國的較量,只有統(tǒng)治者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鞏固法律和軍隊(duì),進(jìn)而穩(wěn)定君主政權(quán)的基礎(chǔ)。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更多的是論述軍隊(duì),武力的重要性及其對意大利統(tǒng)一的重大影響。并且他堅(jiān)定的認(rèn)為好的法律會讓整個國家強(qiáng)盛起來。在論述意大利歷次革命和戰(zhàn)役失敗原因時,馬基雅維利說:“要使得一個新近當(dāng)權(quán)的人能夠獲得巨大的榮譽(yù),莫過于他創(chuàng)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由此可見,馬基雅維利也是十分重視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總之,權(quán)力就是軍隊(duì)和法律,是君主統(tǒng)治權(quán)獲得的基礎(chǔ),是國家秩序穩(wěn)定的最可靠保證。
第三,權(quán)術(shù)論。權(quán)力是政治的核心,攫取權(quán)力本身就是目的。權(quán)力的主體是君主,那么君主如何獲得權(quán)力,如何保持權(quán)力,除了依靠能力之外,君主也必須要懂得“權(quán)術(shù)”,其構(gòu)成了馬基雅維利學(xué)說的另外一個重要部分。而正是由于這個權(quán)術(shù)論,也招致了后人對馬基雅維利的批評與指責(zé)。馬基雅維利強(qiáng)調(diào)不論研究問題還是制定策略,都應(yīng)該從實(shí)際存在的生活出發(fā),而不應(yīng)該從空洞的道德原則出發(fā)。馬基雅維利認(rèn)為,君主為了達(dá)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折手段的。這就是被后人所熟知并遭到眾人抨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其實(shí),我們只有真正的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才可以對他作出評價。正如薩拜因在其《政治學(xué)說史》中這樣說到:“馬基雅維利心目中的君主是機(jī)智與自我節(jié)制的化身,他同樣利用自己的美德和惡癖,這不過是對十六世紀(jì)意大利暴君的理想化寫照而已。他是那種多少有意被夸大了的在暴君統(tǒng)治時代被拋到政治生活前沿的人的真實(shí)寫照。”所以說,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無疑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最后,共和政體思想。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共和政體是一個國家最為理想的政體。馬基雅維利認(rèn)為國家的政體有三種形式,即君主政體,貴族政體還有共和政體。而這三種政體也有可能發(fā)生變異,蛻化成暴君政體,寡頭政體和群氓政體。在諸多的政體中,他認(rèn)為共和政體是最理想的政體。但針對當(dāng)時的意大利,他卻主張實(shí)行君主專制政體,因?yàn)楫?dāng)時意大利需要一個強(qiáng)有力的君主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建立統(tǒng)治和維護(hù)統(tǒng)治是不同的,要實(shí)現(xiàn)理想的共和國是需要在一定的條件的,只有這些條件具備才有實(shí)現(xiàn)的可能,但是在當(dāng)時的意大利,實(shí)現(xiàn)這種政體是非常的困難的。因?yàn)楣埠驼w要以人民的德行和秩序作為前提條件,而意大利市民德行頹廢,社會已經(jīng)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而只有建立君主制,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才能為實(shí)現(xiàn)共和制政體奠定基礎(chǔ)。
三、對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評價
1.對政治學(xué)的影響。馬基雅維利改變了傳統(tǒng)的政治學(xué),讓政治獨(dú)立于道德,使政治學(xué)擁有了現(xiàn)代性。正如馬克思所言:“從近代馬基雅維利以后,權(quán)力都是作為法的基礎(chǔ),由此,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dú)立研究政治的主張,其他沒有別的了。”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改變了西方傳統(tǒng)的政治學(xué)。他在吸收先人優(yōu)秀成果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親身經(jīng)歷和個人經(jīng)驗(yàn)形成了劃時代的偉大思想,進(jìn)行了理論創(chuàng)新,極大地推動了政治學(xué)的發(fā)展。
2.從時代特征的而言,馬基雅維利顛覆了中世紀(jì)傳統(tǒng)的神學(xué)世界觀和道德倫理學(xué)說。他生活在歐洲的舊秩序正在崩潰、國家和社會都面臨不斷迅速出現(xiàn)新問題的時代,試圖解釋這各種事件的邏輯意義,預(yù)測那些不可避免總要發(fā)生的問題,并設(shè)法找到在新產(chǎn)生的種種條件下正在形成的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是注定要在關(guān)系國家生存的今后政治活動中起關(guān)鍵作用。實(shí)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是其畢生的追求,更是新時代的要求。國家統(tǒng)一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這個階段在社會領(lǐng)域的必然要求,馬基雅維利就是這個時代的先驅(qū)者。
3.對當(dāng)時社會的影響。當(dāng)時意大利內(nèi)戰(zhàn)不止,人民希望有一位強(qiáng)有力的君主來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馬基雅維利的呼吁正是順應(yīng)了民心。他的政治思想的目標(biāo)是意大利的統(tǒng)一,實(shí)現(xiàn)途徑是有一個賢明的君主通過建立自己的國民軍,驅(qū)逐外國侵略者。當(dāng)時的意大利,封建勢力頑固,資產(chǎn)階級的力量薄弱,需要王權(quán)的保護(hù)。因此,馬基雅維利主張用君主制來實(shí)現(xiàn)意大利的統(tǒng)一,既符合國情,也順應(yīng)了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
綜上所述,在文藝復(fù)興時期,馬基雅維利一反以前的政治學(xué)家政治思想學(xué)說,開辟了新的政治革命。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客觀的承認(rèn)他那個時代所具有的局限性。馬克思說過,16世紀(jì)以來,許多思想家“都已經(jīng)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他們是從理性和經(jīng)驗(yàn)中而不是從神學(xué)中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guī)律”。馬基雅維利是最早這樣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也擺脫了神學(xué)”。正因?yàn)槿绱耍R基雅維利與古代、中世紀(jì)的政治觀念劃清了界限,成為近代政治學(xué)的奠基人。
參考文獻(xiàn):
[1]徐大同主編.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羅伯特.唐斯著. 纓軍譯: 《影響世界歷史的是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5.
[3]袁繼富:《馬基雅維利政治學(xué)說論析》.理論探討,2007,5.
[4]肖群忠:《論政治權(quán)術(shù)與政治道德的關(guān)系》.齊魯學(xué)刊,1996.
[5]王福春,張學(xué)斌:《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篇2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性;古今之爭;波考克;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對現(xiàn)代性的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近二三十年中國的現(xiàn)代性研究也逐漸起步,在政治思想領(lǐng)域,自由主義有柏林和羅爾斯等為代表,特別是其兩種自由的區(qū)分影響很大;施特勞斯學(xué)派則因隱微寫作與重啟古今之爭而聲名大噪;此外就是劍橋?qū)W派,以以斯金納和波考克為代表,其中波考克雖然在中國不甚知名和流行,但卻是深入理解現(xiàn)代性,特別是古今之爭必不可少的一個路徑。波考克說他“秉持這樣一種歐洲視野:伴隨著古代地中海帝國奔潰歷史的是商業(yè)社會的不斷興起和擴(kuò)展,但與此同時依然受到古代價值的挑戰(zhàn)。”[1]這開啟了他對馬基雅維里時刻的理解。
一、馬基雅維里時刻的意涵
雖然用“時刻”(moment)這一表達(dá)是斯金納的提議,但2003年波考克指出“該術(shù)語(‘時刻’)既可以指馬基雅維里的出現(xiàn)及其對政治思考的沖擊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也可以指他的著作所指出的兩個理想時刻之一:或是指‘共和政體’的形成或奠基成為可能的時刻,或是指這種政體的形成被認(rèn)為帶有不確定性并在它所屬的歷史中引發(fā)危機(jī)的時刻。”[2]
第一個“時刻”,即馬基雅維里活著并寫作《君主論》和《論李維》的時代,具體指“佛羅倫薩思想……1512至1537年,出現(xiàn)了馬基雅維里、圭恰迪尼和詹偌蒂的轉(zhuǎn)折性著作。”[3]這是個佛羅倫薩時刻,馬基雅維里是其中的最強(qiáng)音。另外一個含義則是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熔煉,即《君主論》和《論李維》中包含的“理想”:拯救危機(jī)中的共和國或創(chuàng)建共和國。就具體的歷史而言,指1494年法國軍隊(duì)到達(dá)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統(tǒng)治土崩瓦解之時。馬基雅維里最初是參與到了政治之中的,其寫作《君主論》也懷抱著再次參與政治的期待,但并未成功,這種雄心從政治轉(zhuǎn)移到了寫作。書寫如何“拯救危機(jī)中的共和國”甚至“奠基新的共和國”。波考克認(rèn)為“這樣的時刻彼此無法分割,因而就出現(xiàn)了‘馬基雅維里式的關(guān)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共和國深陷歷史的緊張或矛盾之中,這樣的緊張或矛盾要么出自自身,要么來自外界。”從“時刻”出發(fā)“考察了早期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許多(但不是全部)有關(guān)這種‘關(guān)鍵時刻’的經(jīng)驗(yàn)和關(guān)節(jié)點(diǎn)。”[4]對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的考察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因?yàn)椤拔覀冊庥隽恕埠椭髁x’與‘自由主義’、‘古代’與‘現(xiàn)代’自由概念的差異,在我看來《時刻》所關(guān)注的正是他們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的歷史仍在進(jìn)行中,并沒有終結(jié)”,[5]或說英國在近代也經(jīng)歷了這樣的關(guān)鍵時刻,因而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段政治思想史。
波考克所揭示的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可被理解的。簡要說,有一個理解模式,它有三個要點(diǎn):積極公民、武裝共和國與區(qū)別于“right”(正義或權(quán)利)的“virtue(德行)”。
積極公民是想過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人的總稱,“具有政治知識的即被統(tǒng)治有參與統(tǒng)治的”人,不是純粹被統(tǒng)治的奴仆。這種思想在根底上可以說是“極端的古典思想”,并且“從政治上和道德上說,‘公民生活’是抵抗‘命運(yùn)’肆虐的唯一力量,也是個人具有美德的必要前提。”[6]武裝共和國則是馬基雅維里對古代思想的改造,原型是“武裝的先知”摩西及其所建立的“國”。思想基礎(chǔ)就是“武裝公民”,這是“virtue(德行)”的核心內(nèi)涵,“羅馬意義上的virtue,即馬基雅維里使用并力圖復(fù)興的托斯卡納意義上的virtue的羅馬意涵,意指個人采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能力。”“它既是高度公共性的,也是高度個性化的。”[7]
這個模式也可以被稱為“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思想模式,以此模式衡量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能夠承認(rèn)早期近代英國(英格蘭)政治思想中有許多這種“關(guān)鍵時刻”的經(jīng)驗(yàn)和關(guān)節(jié)點(diǎn)。
二、近代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
從上述思想模式的三個要點(diǎn)看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是一個簡要而非全面的方式,不過從這個三個要點(diǎn)確實(shí)能夠看到一種不同于歐洲大陸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方式。
首先,從積極公民生活這個角度來看,就面臨一個問題,這源自英格蘭自身的歷史,“在這個文化中并沒有出現(xiàn)對‘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相對簡單的選擇以及共和主義對歷史自我形象的改造。” “僅僅理性和經(jīng)驗(yàn)絕無可能提供把個人稱為公民的理由,只有復(fù)活古代的政治‘德性’(virtus)和政治動物(他有著統(tǒng)治、行動和做出決斷的天性)的觀念,才能做到這一點(diǎn)。”[8]這意味英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出現(xiàn)與歷史‘時刻’或說事件――1640年代的內(nèi)戰(zhàn)有關(guān),在其中古典共和主義理論發(fā)揮了它的作用,這種作用是英國“公民”觀念產(chǎn)生的重要部分。
第二個要點(diǎn)即共和國。這與一份文件有關(guān),即1642年6月21日的《陛下對兩院十九條建議的答復(fù)》,它不僅是英國政治思想上一份至關(guān)重要的文獻(xiàn),也是打開馬基雅維里分析之門的鑰匙之一。這份文件有兩個關(guān)節(jié)點(diǎn)意義,一是在英格蘭第一次重現(xiàn)了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政府理論,而這種重現(xiàn)(復(fù)興)也正是1494年后意大利政局步入緊張狀態(tài)的重要思想結(jié)果之一。產(chǎn)生于內(nèi)戰(zhàn)期間的兩個政治思想巨著《利維坦》和《大洋國》,其思考和思想理論的建構(gòu)“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穩(wěn)定與和平。”“自然之路需要和平,和平之路需要服從法律。在英國,法律必須成為大眾的法律,而這些大眾的法律的總和必須等同于共和國。”[9]“英格蘭人從天性上說是贊成君主制和習(xí)俗的動物,采取平衡和共和政體的語言,僅僅是因?yàn)樗麄兊膫鹘y(tǒng)憲法受到了失序的威
脅”。[10]這意味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對佛羅倫薩版將會有不小的修改。
第三點(diǎn),“德行對抗命運(yùn)”這一模式在英國的變換。哈林頓是波考克考察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核心人物。在哈林頓的《大洋國》之前的時刻,“德行”不是道德而是武裝,這是馬基雅維里思想的一個特色內(nèi)容。在16世紀(jì)初期的佛羅倫薩的思想家中,強(qiáng)調(diào)“威尼斯模式”,使“它能夠成為羅馬的反題,因此有助于把人們的注意力從馬基雅維里的軍事平民主義上移開。”不過在英國則不一樣,英格蘭此時的統(tǒng)治就是刀劍的統(tǒng)治。并且“刀劍的時刻可以由君主、立法者或先知占據(jù),也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占據(jù)。”[11]
英國實(shí)際政治中,“有兩點(diǎn)尤其是產(chǎn)生和代表了英國共和主義的思想,首先是對武裝的強(qiáng)調(diào),將政治自由等同于軍事力量;第二個特征是普遍意識到的偶然性,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輝煌,共和政體的生命依然是動蕩的和短暫的。”[12]雖然其目的不過是論證“事實(shí)上的權(quán)力”是克倫威爾的護(hù)國公政權(quán),但是“當(dāng)軍隊(duì)反對這個政權(quán)時,尼德漢姆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處境尷尬,英格蘭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歷史就會有一個新的起點(diǎn)。”[13]這個新的起點(diǎn)就是哈林頓。
哈靈頓在“德行對抗命運(yùn)”的模式中引入了“財(cái)產(chǎn)”,從而促成了這一模式的變換。《大洋國》是哈靈頓的核心作品,“該書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標(biāo)志著突破范式的時刻。”按照馬基雅維里的觀念對英格蘭政治理論和歷史進(jìn)行重要修正。因?yàn)椤八獮橛⒏裉m的軍事共和國辯護(hù),把它說成是‘武裝平民’的統(tǒng)治。”他為此不僅“編造了刀劍的公共歷史”,還“提出了一種公民理論”,“說明英格蘭人是公民,英格蘭的共和國要比自封的圣徒寡頭政體更接近上帝”。“把這些認(rèn)識納入歐洲和英格蘭的政治權(quán)力的一般歷史之中,其基礎(chǔ)是馬基雅維里擁有武裝對于政治人格必不可少的理論。”[14]乃是其關(guān)鍵性創(chuàng)新之處。
武裝平民與積極公民結(jié)合的公民理論,還有一個關(guān)鍵點(diǎn),這就是設(shè)定政治人格的基礎(chǔ)是財(cái)產(chǎn)。哈靈頓對馬基雅維里所強(qiáng)調(diào)的“嚴(yán)重的道德腐敗,公民人格的實(shí)際解體,是政府衰敗的主因”做了重要修正:“政府的‘腐敗’與其說是因?yàn)楣癫辉僬宫F(xiàn)適合于他的美德,不如說是因?yàn)檎螜?quán)威的分配不再與對它其決定作用的財(cái)產(chǎn)分配適當(dāng)?shù)芈?lián)系在一起。”哈靈頓把財(cái)產(chǎn)稱為“命運(yùn)的恩惠”,并且“他特別聲明,他關(guān)于財(cái)產(chǎn)和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一般法則,對動產(chǎn)和不動產(chǎn)同樣適用。”因而“自由財(cái)產(chǎn)的功能變成了為自由的公共行動和公民美德而拿起武器,從而也是人格的表達(dá)。”[15]
簡言之即“自由和獨(dú)立取決于財(cái)產(chǎn)”,因而財(cái)產(chǎn)稱為了一種公民資格,更進(jìn)一步是美德來自于自由財(cái)產(chǎn),因而對抗“命運(yùn)”必須有自由財(cái)產(chǎn),如此而來,對自由財(cái)產(chǎn)的侵蝕就可被理解為“腐敗”這一命運(yùn)的體現(xiàn)物。
在哈靈頓之后,“德行對抗命運(yùn)”的模式先是轉(zhuǎn)換成了“德行對抗腐敗”,在17世紀(jì)晚期和18世紀(jì),出現(xiàn)了一種新觀點(diǎn):“變化現(xiàn)在不在被視為純粹的混亂,而是被視為可以理解的社會和物質(zhì)過程。美德的對立面不再是‘命運(yùn)’,而是變成了‘腐敗’。”腐敗不僅僅指官員的腐敗或生活的腐化,政客收受賄賂濫用權(quán)力等政治腐敗行為,而是“在圭恰蒂尼那兒最先看到的那種含義:用私人權(quán)威取代公共權(quán)威,用依附取代獨(dú)立。”[16]從1688年到1776年,盎格魯語系的政治學(xué)的中心問題,不是能否反抗惡政,而是建立在庇護(hù)權(quán)、公債和軍隊(duì)職業(yè)化上的政權(quán)是否會腐蝕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腐敗不是一個權(quán)利問題,而是一個“德行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申明反抗的權(quán)利得到解決。
政治思想決定性地轉(zhuǎn)向了德行與腐敗的范式。[17]光榮革命后的英國“不論哪個黨派的作者都不想為股票買賣和對公債市場價值的投機(jī)性操作辯護(hù),它(信用)被普遍視為罪惡。”“簡言之,托利黨抨擊牛市,輝格黨抨擊熊市。”[18]爭論的核心點(diǎn)雖然是財(cái)產(chǎn),但實(shí)際上的中心依然是“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因?yàn)椴粍赢a(chǎn)依然被看作是美德的基礎(chǔ),而商業(yè)財(cái)富的重要性雖然被提及,但貿(mào)易被認(rèn)為是新型腐敗的原因,信用更是被公認(rèn)為“邪惡”。
三、反思古今之爭的新路徑
商業(yè)使“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發(fā)生變換乃至改變“德行”本身的含義。商業(yè)帶來的改變看起來不可逆轉(zhuǎn),盡管一些著名思想家都反對這一趨勢,但是商業(yè)社會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德行也借助于“風(fēng)尚”的概念進(jìn)行重新定義,個人脫離了享有公民權(quán)的農(nóng)民-武士世界,進(jìn)入了“商業(yè)和技藝”的交易性世界。這些新的關(guān)系從性質(zhì)上來說是社會關(guān)系而非政治關(guān)系,因此他們使個人能夠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德行”,而只能被稱作“風(fēng)尚”。埃德蒙?伯克說“禮儀風(fēng)尚比法律重要。……它既可襄助道德,補(bǔ)充道德,也能徹底毀掉道德。”[19]
改變“德行對抗命運(yùn)(腐敗)”模式的是商業(yè)社會與自由主義的崛起。人取代了自然,權(quán)利取代了德行,擴(kuò)張性的帝國取代了共和國,最終的災(zāi)難性后果到今天已經(jīng)差不多又快被忘卻了。
篇3
哲學(xué)是客觀環(huán)境在人們的思想中產(chǎn)生的投影,不同歷史時期政治哲學(xué)側(cè)重點(diǎn)都不同,但是都表達(dá)了人們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觀。思想哲學(xué)就是這個時代的精神,人類對現(xiàn)實(shí)的理解與認(rèn)知就是哲學(xué)發(fā)展的根基與動力。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思想政治哲學(xué)都不斷進(jìn)步。比如,西方從古代希臘社會的形而上學(xué)社會政治哲學(xué)基礎(chǔ),到歐洲中世紀(jì)的宗教神學(xué),再到歐洲各國政治變遷的“君權(quán)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xué)主體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響最為深遠(yuǎn),政治上強(qiáng)調(diào)“君權(quán)神授”,社會統(tǒng)治上以“仁、義、禮、信、智”等作為道德規(guī)范基礎(chǔ),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古代政治哲學(xué)以統(tǒng)治階級為服務(wù)對象,不斷發(fā)展與完善以更好地維持統(tǒng)治秩序。近代以來,“社會認(rèn)識論”成為政治哲學(xué)的基礎(chǔ),人類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觀點(diǎn),這時的政治哲學(xué)開始追求社會的平等、公平和正義,在人類社會中表現(xiàn)為追求獨(dú)立自主與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的政治哲學(xué)思想的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完全是按照科學(xué)主義來理解、認(rèn)識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在理論地位上有一定的獨(dú)立性。
二、中國政治哲學(xué)發(fā)展脈絡(luò)
我國思想政治哲學(xué)發(fā)展了幾千年,大致分為了三個階段,即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政治哲學(xué)思想雖然屬于社會意識反映社會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范疇,但在興起與發(fā)展的過程中都具有較大的差異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特點(diǎn)。古代思想政治哲學(xué)針對的社會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的矛盾,其哲學(xué)思想以及社會實(shí)踐手段都是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權(quán)力的統(tǒng)治制度,以維護(hù)少數(shù)人的統(tǒng)治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來,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國社會遭遇巨大變遷,社會現(xiàn)實(shí)導(dǎo)致新的社會政治思想產(chǎn)生,在認(rèn)識論的的基礎(chǔ)上開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會的理性,尤其是資本主義與思想,它在前人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不斷地積累和深化;隨著社會科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與進(jìn)步,人們對于社會規(guī)律的認(rèn)知程度越來越高,科學(xué)的唯物主義已成為我國現(xiàn)代的思想政治哲學(xué)的主流,在政治哲學(xué)中當(dāng)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人們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三、中國古代思想政治哲學(xué)概況
我國自西周時期開始便產(chǎn)生了思想政治哲學(xué),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xué)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對現(xiàn)實(shí)、對人生對道德、對宗教的關(guān)注,并對后世產(chǎn)生了長期且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哲學(xué)思想是為政治服務(wù)的,在處理社會關(guān)系中表現(xiàn)為追求國家的長治久安。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政權(quán)變遷劇烈,朝代更替頻繁,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以及政治穩(wěn)定就是人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思想家、政治家最為關(guān)心、最為迫切的任務(wù)便是如何構(gòu)建一個統(tǒng)一而有序的國家的問題。因而,從政治哲學(xué)形成的起初,社會不同學(xué)派的政治哲學(xué)家、思想家圍繞著這個中心而不斷地創(chuàng)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論,從而構(gòu)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哲學(xué)的基本內(nèi)容。
中國古代思想政治哲學(xué)的基本觀點(diǎn),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觀念等。“大學(xué)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xué)》),“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學(xué)家們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國”既是統(tǒng)治階級對自身施政方式的闡述,也是對社會上下親和關(guān)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創(chuàng)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周公認(rèn)為:“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就是說,“天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來,夏商的滅亡,是因?yàn)樗麄儾恢馈熬吹卤C瘛薄T诖嘶A(chǔ)上,他認(rèn)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戰(zhàn)國時期,即奴隸制衰亡到封建制社會興起時期,子產(chǎn)提出“以寬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對后世的影響較大。儒家主要繼承和發(fā)展了子產(chǎn)的“以寬服民”思想,強(qiáng)調(diào)“德主刑輔”,孔子是從“禮”與“仁”相結(jié)合的思想出發(fā),極力提倡“德治”,認(rèn)為統(tǒng)治者如果能“為政以德”,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統(tǒng)治。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xué)賦予儒家思想理學(xué)的思辯形態(tài),把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發(fā)展到了最高階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但他們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學(xué)說更穩(wěn)居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地位。
而在中國古代社會“法治”思想雖然并未占據(jù)社會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終便隨著政治統(tǒng)治而執(zhí)行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yuǎn),但是受階級的局限性,我國古代的法治卻也只能作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的工具,而難以達(dá)到“公平”、“公正”。
篇4
一、以往思想史研究的誤區(qū)
斯金納認(rèn)為原有的研究者在對觀念史研究時會形成一種錯誤的思維定式,對解讀文本帶來不少的困難,這是因?yàn)椋骸拔覀兞?xí)慣性地會憑借某些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構(gòu)建我們的想法,而這些構(gòu)成了我們思考和理解內(nèi)容的核心因素。”[1]這樣一來,相較于過去對思想家言論的各種研究方式會無法規(guī)避的陷入了各種各樣的歷史謬誤之中。斯金納通過考察傳統(tǒng)觀念史研究方法,認(rèn)為:“通過這些途徑所得出的結(jié)論是神話,并不是歷史。”[2]
1、對學(xué)說神話的批判
斯金納認(rèn)為有的研究者在思想史的研究過程中會陷入了一種稱為“學(xué)說神話”的謬誤中。有的研究者會把思想家在著作中所作的零散的描述結(jié)合為一個整體,并看作是在描寫某一明確的主題。這種做法將會導(dǎo)致時代的誤置這一最大的危險(xiǎn)。還有就是某些研究者認(rèn)定在有關(guān)道德和政治理論的歷史研究領(lǐng)域中會存在某些永恒的標(biāo)準(zhǔn)。這一方法的倡導(dǎo)者是列奧?施特勞斯,他指出探討有關(guān)這些歷史的主體的視角是“明確的逐漸趨于低調(diào)”,這種做法是為了體現(xiàn)對“生活及其目的”的當(dāng)代反思。[3]斯金納指出這種做法對客觀真實(shí)的理解思想家的觀點(diǎn)會產(chǎn)生很大的誤區(qū)。
2、對連貫性神話的批判
斯金納指出連貫性神話在向兩個錯誤的方向演化:其一是某些研究者為了挖掘出最大限度的連貫性,經(jīng)常會歪曲思想家本人在論述某一主題上的意圖,有的研究者甚至?xí)o視那些不利于維系連貫性的論述;其二是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觀點(diǎn)時,一些研究者會遇到一些障礙,這些障礙雖不利于維系經(jīng)典文本內(nèi)在的連續(xù)性,但他們并不認(rèn)為這是實(shí)質(zhì)的障礙。因?yàn)樗麄冋J(rèn)為文本中并不存在真實(shí)的障礙。而以上的研究方法將不可避免地使研究者誤入了目的在于“解決自相矛盾”的經(jīng)院式歧途。斯金納認(rèn)為以上這些都是錯誤的研究方法。
3、對預(yù)期神話的批判
斯金納認(rèn)為當(dāng)我們利用思維定勢去解讀思想家某一特定時期的觀點(diǎn),而不是解讀其在描述特定言論對象的意涵時,預(yù)期神話就容易滋生。這種做法將會導(dǎo)致這樣一種誤區(qū),即研究者也許會利用慣性思維在一些不熟悉的著作中發(fā)現(xiàn)一些熟悉的論述,將思想家的觀點(diǎn)標(biāo)簽化,把以往理解的觀點(diǎn)與現(xiàn)在研究的觀點(diǎn)生硬的對接,進(jìn)而對正確解讀文本意涵產(chǎn)生歧義。這也不是研究思想史應(yīng)該采用的方法。
二、“劍橋?qū)W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主流方法
斯金納提倡我們在理解并解讀經(jīng)典文本時,不單單是準(zhǔn)確的解釋思想家所要表達(dá)觀點(diǎn)的意涵,更要格外注意的是能夠清楚地把握該思想家闡述思想的語境。這是因?yàn)橐粋€思想家在不同時期對某一問題的看法有可能是不同的。
1、意涵
思想家論述所要表達(dá)的意涵是要領(lǐng)會其意圖的第一個要素。重視意涵在解讀文本時的作用非常關(guān)鍵,因?yàn)橐夂抢斫馑枷爰乙匝孕惺碌年P(guān)鍵。由于思想家常常故意采用一套拐彎抹角的修辭策略,即言說和意思的分離,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對文本進(jìn)行解讀是不可取的,只能通過理解著作家的意涵才能實(shí)現(xiàn)。“就一切正式的論斷而言,僅僅憑借一家之言并不足夠幫助我們理解作者言說的意涵。要完整準(zhǔn)確理解某一論斷,我們不僅需要掌握作者想要表達(dá)的意涵,而且同時要把握這一言說的意欲效應(yīng)。換言之,不但要理解人們的言說,而且要理解人們的言說行動”,[4]而研究過去的思想史的意涵與意欲效應(yīng)只是兩大詮釋任務(wù)的第一步。
2、語境
要領(lǐng)會作者意圖的第二個要素是應(yīng)當(dāng)在特定的語境中考察特定的言論,進(jìn)而把握作者特定的寫作意圖。我們唯有將與文本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語境系統(tǒng)進(jìn)行復(fù)原,尋找最初產(chǎn)生文本的脈絡(luò),才能真正徹底的理解隱藏于文字之下的思想家的真實(shí)意圖。斯金納強(qiáng)調(diào),我們只有將所研究的文本與特定的語境嚴(yán)絲合縫的對接,才能用不產(chǎn)生歧義的、正確的方法來解讀思想家的某些觀點(diǎn)。這才會有利于我們進(jìn)一步辨識那些思想家寫作時的言語行動。也就是說,我們雖然不可能完全進(jìn)入已經(jīng)距今幾百年或幾千年思想家的生活中真切的考察,但是我們可以借助語境和言語行動去把握思想家的觀點(diǎn),對他們不同時期的同一個觀點(diǎn)進(jìn)行比較,對他們的想法進(jìn)行復(fù)原,以及能夠不用慣性思維而是設(shè)身處地的解讀他們的思想。
三、結(jié)語
“劍橋?qū)W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納“闡述了關(guān)于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現(xiàn)狀與政治理論的不滿,并從方法論的角度掀起了革故鼎新的思潮。”[5]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在西方思想領(lǐng)域中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改變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通過斯金納的方法,不僅可以知道作者的論述過程,更有希望了解作者的寫作特點(diǎn),所要回答的問題,以及他們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贊許、質(zhì)疑或者駁斥。更重要的是,用“劍橋?qū)W派”所倡導(dǎo)的研究方法進(jìn)行解讀文本時會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鋪墊,因?yàn)椋骸爱?dāng)研究者以‘劍橋?qū)W派’所倡導(dǎo)的方法解讀一部著作的寫作意涵時,這不僅是在為他們的解讀提供相關(guān)背景,而是已經(jīng)是在進(jìn)行解讀本身的工作”。[6]
【注 釋】
[1][2][4] [英]昆廷 斯金納.任軍峰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載于丁耕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7.99.127.
[3] [美]施特勞斯. 李天然等譯.政治哲學(xué)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042-1043.
篇5
關(guān)鍵詞:《民初留英學(xué)人的思想世界》;書評;五四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Z121.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學(xué)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以下簡稱陳著),陳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出版。
在推進(jìn)近代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進(jìn)程中,中國留學(xué)生在東西文明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作用,對于實(shí)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至關(guān)重要。可以說,沒有中國留學(xué)生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對新思想的傳播,中國難以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轉(zhuǎn)換。陳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學(xué)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全書30余萬字。該書對于從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學(xué)人群體的活動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討論多有前人所未發(fā)之處,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運(yùn)用方面,亦有進(jìn)一步討論的余地。概而言之,陳著有如下四點(diǎn)創(chuàng)新之處。
一、對以往較少關(guān)注的知識群體的發(fā)現(xiàn)
近代中國的改革運(yùn)動,深深烙印著中國留學(xué)生的印記,從不同國家歸來的中國留學(xué)生群體都有著不同的群體特征。在內(nèi)憂外患的近代中國,在傳統(tǒng)的中華文化中找不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之時,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國家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隨著留學(xué)生的人數(shù)增長,帶著西方新思想的歸國留學(xué)生越來越對產(chǎn)生了巨大的推動與引導(dǎo)作用。其中幾個主要留學(xué)國家對于中國的改革運(yùn)動的影響尤為深刻。對中國影響最為深刻的國家是當(dāng)時最為強(qiáng)盛的大英帝國,當(dāng)時著名的翻譯家林紓的三分之二的譯著都來自英國文學(xué),而嚴(yán)復(fù)的全部譯著都來自英國著作。到了19世紀(jì)與20世紀(jì)之交,隨著幾個美國、日本、法國不同國家的中國留學(xué)生的增多,美國、日本、法國對于中國的影響逐漸增強(qiáng),相對而言英國對中國的影響逐漸變小。具有不同國家留學(xué)背景的留學(xué)生歸國后積極宣傳自己的所學(xué)所思,都帶有不同國家的文化、政治、經(jīng)濟(jì)特點(diǎn)。在當(dāng)時倡導(dǎo)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浪潮無疑對中國政治、文化、經(jīng)濟(jì)等方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學(xué)背景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進(jìn)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學(xué)背景的學(xué)人對于思想發(fā)展的影響。
與留美學(xué)生、留日學(xué)生、留法學(xué)生相較,留英學(xué)人對五四時期的政治與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陳著認(rèn)為僅從“影響”的角度來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xiàn)是狹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間留英學(xué)人的思想發(fā)展是一種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義的。更為重要的,留英學(xué)人成為陳著的研究對象除了“時常出現(xiàn)”“思想邏輯上有其意義”,這個群體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陳著指出:“在精神狀態(tài)上,留英中國學(xué)人既具有傳統(tǒng)中國士大夫憂國憂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們曾經(jīng)比較系統(tǒng)地接受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間,中國的啟蒙運(yùn)動的倡導(dǎo)者們對于思想運(yùn)動有著極強(qiáng)的緊迫感,因此在思想啟蒙運(yùn)動中也常常夾著感性與混亂。1921年杜威在《亞洲》雜志上指出:“這場運(yùn)動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還伴隨有夸張、混亂以及智慧與荒謬的雜合。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這場運(yùn)動在開始階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學(xué)人主張學(xué)習(xí)西方,英國19世紀(jì)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發(fā)展都與留英學(xué)人思想發(fā)展有著深層的關(guān)聯(lián)。在這場思想大啟蒙運(yùn)動中,留英學(xué)人更加重視對學(xué)術(shù)理論的討論,對國際時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學(xué)人在地方主義和聯(lián)省自治、對于一戰(zhàn)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國際主義的探討都極大豐富了思想的廣度和深度。也因此,才顯得留英學(xué)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們加重視學(xué)術(shù),使得他們對中國政治思想的貢獻(xiàn)和作用更為持久。
在研究對象的視角方面,陳著也有著新亮點(diǎn)。學(xué)界對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個體為研究對象。以自由主義思想研究為例,學(xué)界往往局限于個體自由主義者的研究,沒能從個體中研究他們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難達(dá)成一致意見。而陳著通過具體探析個體留英學(xué)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學(xué)人作為整體研究對象,開拓了研究視角,對思想史研究具有啟發(fā)意義。
二、國際史研究方法的嘗試
陳著指出:“所謂‘國際史’,是傳統(tǒng)外交史領(lǐng)域下的一個新興子學(xué)科。與傳統(tǒng)外交史方法不同,國際史是要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而將整個世界作為研究框架。它關(guān)注的是大歷史,即除了傳統(tǒng)外交史問題,文化和社會也是關(guān)注對象;還探討國際權(quán)力體系和某種特殊文化觀之間、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民族抱負(fù)和集體失意之間的關(guān)系。”中國近代的發(fā)展進(jìn)程正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推進(jìn)的,中國的政治革命、思想運(yùn)動往往是受到了資本主義全球擴(kuò)張的刺激并結(jié)合自身實(shí)際而產(chǎn)生的反應(yīng)。的發(fā)生正是一戰(zhàn)后的國際大背景的刺激而發(fā)生的。因此通過時人尤其是有著扎實(shí)學(xué)理基礎(chǔ)的留英學(xué)人對于國際政治的思考對于了解國內(nèi)政治、思想運(yùn)動的國際背景有著重要的作用。陳著運(yùn)用了國際史的研究方法,還運(yùn)用史料實(shí)證研究,從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學(xué)人政治思想上的反應(yīng)。首先,陳著闡釋了留英學(xué)人對于當(dāng)時主要國家的政治運(yùn)動與思潮的思考,關(guān)于戰(zhàn)時大英帝國的政治改革;關(guān)于俄國革命及其演變;關(guān)于美國、日本問題;關(guān)于戰(zhàn)后的“代議制之改造”思潮。這些國際主要政治運(yùn)動與思潮刺激著留英學(xué)人,對留英學(xué)人的國內(nèi)政治改革有很大啟示。其次,陳著以《太平洋》雜志為中心,闡釋了留英學(xué)人面對“五四”前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過程,對于國際政局的判斷,并由此表達(dá)的對外態(tài)度和政治主張:關(guān)于參戰(zhàn)論和修約論,關(guān)于警惕日本的侵華政策,關(guān)于與英美合作,關(guān)于“親俄”的外交主張:“主張戰(zhàn)后中國應(yīng)開展主動外交,不畏事,多嘗試,努力收回國權(quán),并維護(hù)不受侵犯;同時積極于戰(zhàn)后國際社會中尋求一個正當(dāng)?shù)膰H地位,然后才能發(fā)揚(yáng)國際主義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chǔ)上,與其他國家進(jìn)行合作。”最后,陳著論及留英學(xué)人的國際主義思想。留英學(xué)人對于威爾遜等的國際主義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并對戰(zhàn)后國際聯(lián)盟的成立和中國參與抱以關(guān)注的態(tài)度。陳著作提醒:“留英學(xué)人對國際主義及國際聯(lián)盟的認(rèn)識和接受,似乎與“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義思潮并不相容,但他們以國際主義作為攻守的武器,爭取中國的國家和國家人格的意識卻值得注意。”學(xué)界對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國內(nèi)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個國際的思想背景以及國內(nèi)思想運(yùn)動的國際思想資源。在近代國際關(guān)系對中國國內(nèi)政治、思想運(yùn)動走向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以國際史的視角研究留英學(xué)人的國際主義、國際政治觀,為我們思考當(dāng)時國內(nèi)政治、思想運(yùn)動提供了全面的國際背景和思想資源。
三、對非核心報(bào)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個復(fù)雜現(xiàn)象,“它不是一個單純不變,組織嚴(yán)密的運(yùn)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期間并非沒有主流”[3]。在許多研究者看來,思想史經(jīng)過90多年的研究,學(xué)界所著論文書刊可謂汗牛充棟,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種單線挖掘。陳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現(xiàn)狀,指出:“對五四時期的核心材料、領(lǐng)導(dǎo)性的社團(tuán)的過度詮釋也已經(jīng)形成一些學(xué)者所詬病的無所不包的‘史’歷史敘述的架構(gòu)。在這種架構(gòu)下,對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動’,迄今學(xué)者的研究雖然不少,但是整體上仍為《新青年》的強(qiáng)勢話語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成為一種強(qiáng)勢話語。但是,陳著也指出:“對思想、倫理、道德問題的重視并非五四知識分子言論的全部內(nèi)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五四時期,依然存在著從政治法律、財(cái)政經(jīng)濟(jì)、社會問題以及國際政治與外交等方面來思考中國問題的思想言說。”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與其他史料互相印證,這種管中窺豹的歷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還原歷史的全貌。對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須將其置于晚清以降的報(bào)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敗得失。
陳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雜志。之所以選用此兩份雜志,一則正是對于學(xué)界既往研究側(cè)重于“史”模式的影響,對于核心雜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對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雜志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因而容易產(chǎn)生疏漏。再則,之所以選用《甲寅》、《太平洋》雜志是作者考證兩份雜志發(fā)現(xiàn),沒有把聚攏在《甲寅》、《太平洋》雜志上的留英學(xué)人視作一個“自在”的社群。“結(jié)合兩份雜志宗旨所見,這些材料與留歐學(xué)生在法國創(chuàng)辦的《旅歐雜志》,留美生在美國創(chuàng)辦的《留美學(xué)生月報(bào)》不同,它們是留英學(xué)人有意識地模仿英國的《愛丁堡評論》,希望做成中國的獨(dú)立評論雜志。還有一點(diǎn)不同,它們都是由已經(jīng)歸國的留英學(xué)人創(chuàng)辦、編輯,并在國內(nèi)出版,而在讀的留英學(xué)人亦積極參與,這一點(diǎn)說明它們與國內(nèi)的社會政治思潮的聯(lián)系有著更為密切的聯(lián)系。”留英學(xué)人注重觀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論,謀求國家的發(fā)展。因此,陳著依據(jù)《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學(xué)人主持的同仁雜志,梳理這一社群聚攏的歷史過程以及他們在內(nèi)政改革與走向世界兩個面向上的思想規(guī)劃;同時將留英學(xué)人的思想世界與“史”對接,這對于豐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四、加深對英式經(jīng)驗(yàn)主義的認(rèn)識
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為解決當(dāng)今現(xiàn)實(shí)問題的思想借鑒,是思想史研究的意義所在。陳著強(qiáng)調(diào),留英學(xué)人更加重視對于學(xué)理的思考以及國際政局的考量,因此對于探求中國立國之道更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遺產(chǎn)在當(dāng)今更具有參考價值。陳著指出:“民初留英學(xué)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兩個面向,一是內(nèi)向的政治改革規(guī)劃,從關(guān)注中央層面的內(nèi)閣、國會等,到呼吁地方層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動聯(lián)省自治運(yùn)動;另一個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規(guī)劃,在外交上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爭取國家完整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英國作為近代自由主義最先得到發(fā)展的國家,自然對于留英中國學(xué)人的思想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陳著論述了西方理論、內(nèi)閣制和比較溫和的“調(diào)和立國論”,并且在第四章重點(diǎn)討論了留英學(xué)人的地方主義與聯(lián)省自治。這些自由主義思想豐富了尋找立國之道的思想內(nèi)容,助推了的思想啟蒙運(yùn)動,對于當(dāng)今尋找立國之道也有其現(xiàn)實(shí)意義。同時,留英學(xué)人重視研究國際時局以及如何處理各個國家的關(guān)系,探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對國家的進(jìn)步是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
近年來,留學(xué)史的研究受到了學(xué)界的重視,獲得了頗為的成果,但在眾多的學(xué)術(shù)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卻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學(xué)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實(shí)專注于史料的解讀以獲新知,所獲定是良多。陳友良先生便是這樣一位學(xué)者,采治學(xué)之新方法,專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獲頗豐。
參考文獻(xiàn):
〔1〕陳友良.民初留英學(xué)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國啟蒙運(yùn)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chǎn)[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