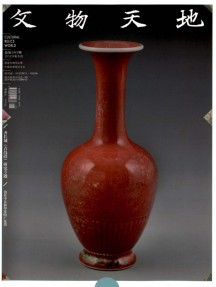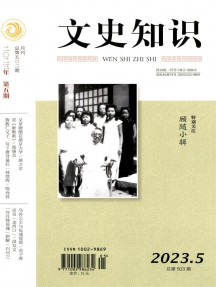考古學(xué)文化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shí)間:2023-11-10 10:13:01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shí)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考古學(xué)文化,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關(guān)鍵詞: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類型、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hào):K8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xué)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畢業(yè)于四川大學(xué)考古學(xué)專業(yè)的知名學(xué)者,對(duì)其著作進(jìn)行研讀,對(duì)我們的學(xué)習(xí)、研究具有極強(qiáng)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領(lǐng)域有極高的造詣,對(duì)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獨(dú)到之處。故選擇論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guān)系研究檢視》、《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jìn)行精讀。三篇文章分別從考古學(xué)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xué)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及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三個(gè)問題展開。這三個(gè)問題,無論是在考古學(xué)理論研究還是在田野考古實(shí)踐中都是時(shí)常碰到的核心問題。本文分別從文章的主要內(nèi)容、觀點(diǎn)等方面做介紹。
一、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
《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曾發(fā)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該文主要從四個(gè)方面展開論述,系統(tǒng)的介紹了學(xué)界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文章第一部分,詳細(xì)介紹夏鼐先生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這一問題做出指導(dǎo)意見的具體論述及相關(guān)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舉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獨(dú)到見解,如:指出應(yīng)在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原則中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文章第三部分,介紹各家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三要素” 的觀點(diǎn),同時(shí)指出考古學(xué)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創(chuàng)新之處,提出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的確認(rèn)要通過國家級(jí)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如中國考古學(xué)會(huì)),并詳細(xì)闡述了“命名確認(rèn)”的程序。
二、區(qū)系類型問題的研究―《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guān)系研究檢視》
《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guān)系研究檢視》一文曾發(fā)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該文主要從四個(gè)方面展開論述。文章主要圍繞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確立及關(guān)系問題展開論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紹了1959年,類型劃分問題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廟底溝、后者早于前者、兩者同時(shí)并存這三種說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點(diǎn)介紹了廟底溝早于半坡這一最初的簡單論證,安志敏、馬承源學(xué)者的觀點(diǎn)。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紹了一個(gè)完全相反觀點(diǎn)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個(gè)簡要的地層關(guān)系報(bào)告,它對(duì)兩類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個(gè)新論證,即同時(shí)并存(犬牙交錯(cuò)的兩個(gè)類型)。
三、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淵源的解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
《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曾發(fā)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從文章題目可知該文重點(diǎn)探討仰韶文化“淵源”,即仰韶文化的“源頭”問題。該文主要從五個(gè)方面展開敘述。第一部分,80年代確定仰韶文化源頭的歷程。安特生將河南、甘肅發(fā)現(xiàn)的彩陶,同中亞土庫曼的安諾文化彩陶進(jìn)行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梁思永先生發(fā)現(xiàn)了安陽后崗“三疊層”,尹達(dá)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來說”、“六期說”。但仰韶文化的來源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第二部分,從多源觀到一源觀。“分源”問題的提出,是一個(gè)重大突破。嚴(yán)文明、張忠培先生發(fā)表了相似的“分源”觀點(diǎn),嚴(yán)文明先生建議將仰韶文化“一分為二”,將后崗―大司空和半坡―廟底溝作為兩個(gè)不同系統(tǒng)區(qū)分開來。第三部分,關(guān)于仰韶文化與仰韶體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來源,追本最為切要。目前學(xué)界構(gòu)建的大仰韶文化體系內(nèi)涵并不是單一的,內(nèi)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將隴東―關(guān)中―陜南―豫西中心區(qū)的仰韶文化,分別命名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嶺下層劃為前仰韶文化。周邊分布區(qū)分別命名后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來源問題。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灣、老官臺(tái)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來源。同時(shí)“北首嶺類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過渡的一個(gè)中間類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淵源,但北首嶺類型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缺環(huán)。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紀(jì)沒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幾點(diǎn)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確認(rèn)”程序)中提出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的確認(rèn)要通過國家級(jí)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如中國考古學(xué)會(huì)),并詳細(xì)的闡述了“命名確認(rèn)”的程序。這是他的創(chuàng)新之處。
2、通過這三篇文章的閱讀,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出發(fā)點(diǎn)分別介紹了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及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考古學(xué)文化淵源的探索問題。這三個(gè)問題在考古學(xué)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終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學(xué)文化研究的核心內(nèi)容,也是我們?cè)诳脊艑?shí)踐中常常遇到的問題。那么,我們將運(yùn)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進(jìn)行考古學(xué)文化研究呢?
3、欲對(duì)一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進(jìn)行研究應(yīng)當(dāng)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間范圍和時(shí)間幅度。這項(xiàng)研究中通常要用到類型學(xué)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層學(xué)的運(yùn)用。
4、同樣的地層,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結(jié)論?王先生在《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guān)系研究檢視》一文中指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xué)和類型學(xué)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證據(jù)確鑿,結(jié)論卻大相徑庭。為何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問題的癥結(jié)究竟在哪里,怎樣解決,現(xiàn)在似乎還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shí)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總結(jié)出一些方法和經(jīng)驗(yàn)來。在考古學(xué)研究中,地層學(xué)和類型學(xué)是基本理論,關(guān)于這兩個(gè)理論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內(nèi)容上文已做詳細(xì)闡述,但是如何正確熟練的運(yùn)用這些理論卻是一個(gè)較難的問題。
5、通過閱讀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及考古學(xué)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但是這也是我們不斷改進(jìn)研究方法的動(dòng)力,前人在探索過程中耗費(fèi)的時(shí)間和精力,他們長時(shí)期的堅(jiān)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借鑒的地方。
參考文獻(xiàn)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
[2]嚴(yán)文明:《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研究中的兩個(gè)問題》,《文物》1985年8期。
[3]張忠培:《研究考古學(xué)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gè)問題》,《中國考古學(xué):實(shí)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shí)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馬承源:《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問題》,《考古》1961年7期。
[6]楊建芳:《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分期》,《考古學(xué)報(bào)》1962年1期。
[7]蘇秉琦:《地層學(xué)與器物形態(tài)學(xué)》,《文物》1982年4期。
[8]張忠培:《地層學(xué)與類型學(xué)的若干問題》,《中國考古學(xué):實(shí)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篇2
關(guān)鍵詞: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開篇指出文章內(nèi)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學(xué)文化這一考古學(xué)家的主觀行為而引發(fā)的一些分歧需要確立對(duì)其命名的原則及程序以盡可能的使它規(guī)范化。為了避免分歧達(dá)成共識(shí),我們需要確立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準(zhǔn)則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個(gè)部分,分別為“夏鼐‘命名四原則’”;“命名分歧”;“考古學(xué)文化‘三要素’”;“‘命名確認(rèn)’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則’”先簡要概括了中國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所經(jīng)歷的變化過程并轉(zhuǎn)述了夏鼐先生20世紀(jì)提出的一個(gè)成熟的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三原則”。第一,一種文化必須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類型的一直最好發(fā)現(xiàn)不止一處;第三,必須對(duì)這一文化的內(nèi)容有相當(dāng)充分的認(rèn)識(shí)。在此需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是作者在三原則之后綜合學(xué)術(shù)界主流觀點(diǎn),考古學(xué)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觀點(diǎn),歸納出第四個(gè)命名條件:以首次發(fā)現(xiàn)的典型遺址的小地名命名。強(qiáng)調(diào)“確定考古學(xué)文化的名稱,既要求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的遺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遺址,面對(duì)幾種選擇時(shí),定名要適當(dāng)”①。關(guān)于作者自己總結(jié)的第四條原則,安志敏先生在《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及其命名問題》中也有提到:“根據(jù)考古學(xué)研究的慣例,一般是用最初發(fā)現(xiàn)的典型地點(diǎn)或富有特征的遺跡、遺物來命名”②。這不乏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與實(shí)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時(shí)也說:“盡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發(fā)現(xiàn)的典型地點(diǎn)為原則, 由于某些特殊情況也出現(xiàn)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臺(tái)文化舉例說明。這就是第二部分要講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學(xué)界對(duì)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原則并無明顯異議,但在理解過程和實(shí)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舉例分別列舉了幾種分歧現(xiàn)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嚴(yán)文明先生強(qiáng)調(diào)約定俗成但應(yīng)在新發(fā)現(xiàn)和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上重新進(jìn)行概括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嚴(yán)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研究的兩個(gè)問題》中談到:“考古學(xué)文化史客觀存在的,對(duì)一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的發(fā)現(xiàn)與認(rèn)識(shí)卻是逐步完成的”④。嚴(yán)先生認(rèn)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典型遺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來會(huì)發(fā)現(xiàn)其實(shí)它不處于此考古學(xué)文化的中心地帶。其次談及張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強(qiáng)調(diào)“第一次發(fā)現(xiàn)的典型遺跡”中得“典型”。張先生嚴(yán)格規(guī)范了典型遺址的標(biāo)準(zhǔn)尤其強(qiáng)調(diào)其中第三點(diǎn):考古工作必須有一定的質(zhì)量及規(guī)模。
上述兩種觀點(diǎn)是在贊同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細(xì)部的分歧。近年來,不乏有學(xué)者否定這種以典型遺址命名的方法。像張國碩先生認(rèn)為,在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進(jìn)行命名時(shí),應(yīng)堅(jiān)持以首次發(fā)現(xiàn)的遺址命名,避免“典型遺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遺址的選擇很難把握,但首次發(fā)現(xiàn)的遺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來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對(duì)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則”的一點(diǎn)看法。作者認(rèn)為夏鼐先生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原則不夠具體,“例如他沒有明確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沒有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器物群至少應(yīng)包括幾種器型”⑤,并指出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圍越劃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作者以仰韶文化為例,對(duì)中國考古學(xué)中文化命名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了具體的分析,尤其重點(diǎn)討論了對(duì)仰韶文化的類型研究中有的學(xué)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賢先生認(rèn)為仰韶體系過于龐大,提出的一個(gè)解決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認(rèn)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關(guān)中地區(qū)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臺(tái)文化發(fā)展而來的客省莊二期文化;河南地區(qū)由裴李崗文化發(fā)展而來的龍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晉南關(guān)中東部由磁山文化發(fā)展而來的后崗二期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并依次對(duì)其命名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學(xué)文化‘三要素’”先通過羅列夏鼐,安志敏,張忠培,嚴(yán)文明等學(xué)者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的定義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學(xué)者們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的定義基本沒有分歧,并通過柴爾德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時(shí)間,空間,特征。作者認(rèn)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過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時(shí)空維度常常是通過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導(dǎo)出來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論證了要研究透徹“三要素”之后才為某支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是不現(xiàn)實(shí)的。表明“特征的確認(rèn),才是考古學(xué)文化確立的關(guān)鍵”并且用這個(gè)觀點(diǎn)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該以首次發(fā)現(xiàn)命名還是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問題。答案就是看此遺址是否體現(xiàn)所要命名的考古學(xué)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確認(rèn)’程序”是作者個(gè)人對(duì)命名確認(rèn)提出的一系列具體實(shí)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學(xué)者們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內(nèi)涵無明顯分歧,在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在具體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問題,隨后提出自己的設(shè)想:作者認(rèn)為考古學(xué)界應(yīng)該建立一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委員會(huì)”,給予其審定命名的權(quán)利。只有通過審定的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才可以公開出現(xiàn)。筆者認(rèn)為此種設(shè)想確實(sh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hù)考古學(xué)文化的純潔性。對(duì)“‘命名確認(rèn)’程序,作者提出了一個(gè)比較具體的方案:首先必須在原則上進(jìn)行審查,并且依據(jù)進(jìn)程適時(shí)調(diào)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個(gè)部分,學(xué)者提出命名申請(qǐng)命名委員會(huì)召開會(huì)議審議,如有異議可暫緩議決或采取投票表決對(duì)考古學(xué)新文化的命名審議通過后要“命名確認(rèn)書”之類的公告。隨后作者談及考古學(xué)界關(guān)于命名確認(rèn)的現(xiàn)狀,夏鼐先生和尹達(dá)先生提過用群眾路線解決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見實(shí)行。對(duì)于如何解決命名分歧問題,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對(duì)于新發(fā)現(xiàn)的考古遺存……如果產(chǎn)生爭議, 也可以通過討論或?qū)W術(shù)會(huì)議的裁定, 來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⑦這些年的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一直處在一種較不規(guī)范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中。
最后,作者說道:“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在事實(shí)上還能通過淘汰過程實(shí)現(xiàn)優(yōu)化……但是這個(gè)自然淘汰過程顯得過于漫長”⑧。筆者個(gè)人也很期待考古學(xué)界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建立起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的權(quán)威機(jī)構(gòu),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設(shè)想的那樣,使今后的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在規(guī)范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下進(jìn)行。
綜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一文結(jié)構(gòu)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個(gè)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的整體框架,環(huán)環(huán)緊扣,用整理歸納出來的學(xué)者觀點(diǎn)將其充實(shí),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匠心獨(dú)運(yùn),提出自己獨(dú)到的見解看法,例如建立一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委員會(huì)”,有助于解決考古學(xué)文化命名分歧的問題。
參考文獻(xiàn):
[1] [5][6][8]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4] 嚴(yán)文明《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研究的兩個(gè)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關(guān)于考古學(xué)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嚴(yán)文明《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研究的兩個(gè)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xué)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篇3
關(guān)鍵詞:中國文明起源;遼西地區(qū)古文化;新石器時(shí)代
首先要明確兩個(gè)概念。一是本文所談及的國家文明起源,時(shí)間上中國早期國家文明萌芽于2500BC左右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時(shí)代,空間上不僅限于中原一帶,其他地區(qū)也存在文明起源中心,如北方遼河流域。二是本文所界定的遼西地區(qū),是指以西拉木倫河流域?yàn)橹行模髌鹧嗌轿鞫危仄呃蠄D山、努魯虎爾山、巫醫(yī)閭山向東至遼河平原;從大興安嶺南麓起涵蓋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教來河、大小凌河、灤河,自北向南基本上包括了遼寧省西部、內(nèi)蒙古東南部和京津冀三省市北部地區(qū)。遼西地區(qū)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在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就形成了有異于東北其他地區(qū)且相對(duì)穩(wěn)定的文化格局,目前這一地區(qū)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遺存有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年代從距今8000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故本文從影響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這一角度出發(fā),從以下幾個(gè)方面展開探討。
一、農(nóng)業(yè)的發(fā)生
人類在走向文明的進(jìn)程中,由于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形成了長期定居的村落,從而為步入文明社會(huì)的正軌奠定了所需的物質(zhì)基礎(chǔ)。因此可以說,中國傳統(tǒng)的早期國家是根植于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的農(nóng)業(yè)文明[1]。從地理位置上看,遼西地區(qū)地處中原農(nóng)業(yè)和東北漁獵經(jīng)濟(jì)類型的中間地帶,河湖與丘陵密布,氣候溫暖濕潤,是典型的混合經(jīng)濟(jì)、人群雜居地帶。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的興隆洼文化經(jīng)濟(jì)類型以狩獵―采集―漁獵為主,早期不見農(nóng)業(yè),在中后期發(fā)現(xiàn)有已碳化的人工栽培谷物1500余粒,是目前世界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粟類谷物顆粒實(shí)物遺存[2]。由此可見農(nóng)業(yè)在該文化時(shí)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補(bǔ)充性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與狩獵―采集―漁獵經(jīng)濟(jì)類型相結(jié)合從而形成一種復(fù)合型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其次,該文化出土的有肩石鋤和長方形或亞腰形石鏟,也都具有翻整土地的農(nóng)業(yè)用途;此外,在房址居住面上還普遍發(fā)現(xiàn)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3]。
按現(xiàn)在的流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農(nóng)業(yè)的發(fā)生和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使得社會(huì)有能力供養(yǎng)更多的人口,實(shí)現(xiàn)聚群而居,促使國家文明的到來。由此可見,這種較早發(fā)生在遼西地區(qū)的北方旱地粟作農(nóng)業(yè)對(duì)于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意義。
二、聚落形態(tài)和防御性設(shè)施
伴隨農(nóng)業(yè)的發(fā)生,人類的居住形態(tài)過渡到定居的村落;由于國家文明的出現(xiàn),具有防御功能的城也隨之興起。學(xué)術(shù)界一般將遼西考古發(fā)現(xiàn)的興隆洼文化聚落[4]分為三期:一期以興隆洼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遺存為代表;二期以興隆洼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臺(tái)子及興隆溝聚落遺存為代表;三期以白音長汗聚落遺存為代表。聚落由居住區(qū)、燒窯區(qū)、墓葬區(qū)和祭祀?yún)^(qū)組成,各區(qū)分工明確,聯(lián)系緊密,形成了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經(jīng)濟(jì)和精神文化體。居住區(qū)為凝聚式格局,房屋多為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積存在大、中、小之別;有環(huán)壕聚落和非環(huán)壕聚落兩種,其前者數(shù)量居多;還可以分為單體聚落和多體聚落兩種,每處聚落都有中心房址。帶壕聚落有三種類型,一種是以興隆洼一期聚落為代表,環(huán)壕平面近圓形,西北側(cè)留有出口,寬2米 ,深1米左右;一種是北城子聚落遺存為代表三面環(huán)壕,一面向水;還有一種為雙壕各環(huán)繞一個(gè)居住區(qū),以白音長汗遺址興隆洼文化乙類聚落為代表,環(huán)壕平面近圓形,橫剖呈倒梯形,現(xiàn)存的溝深和寬度均1米左右不到2米。由此可見,興隆洼文化聚落的環(huán)壕可能兼具一定的防御性能和分區(qū)功能,尤其是北城子聚落遺存的設(shè)計(jì)更凸顯了圍壕的防御性能。
在興隆洼文化接近尾聲之際,西拉木倫河以南取而代之的是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兩種文化基本上交錯(cuò)并存,但從出土的陶器面貌上看,趙寶溝文化與興隆洼文化之間可能存在更密切的先后繼承關(guān)系。已發(fā)掘的趙寶溝文化遺存規(guī)模較小共6處,且多為居住址,從已發(fā)表的白音長汗遺址、水泉遺址、小山遺址和趙寶溝遺址材料上看,房屋均為成排分布的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依據(jù)房屋的數(shù)量可分為大、中、小三個(gè)類型:趙寶溝遺址面積9萬平米以上,房屋數(shù)量100余座,且劃分有居住區(qū)和祭祀?yún)^(qū),是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中心性聚落;水泉遺址房屋有30多座,屬中型聚落;小山遺址和白音長汗遺址房屋總和不足10座,為小型聚落[5]。趙寶溝文化的三種聚落形態(tài)均經(jīng)統(tǒng)一規(guī)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已存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社會(huì)組織。并對(duì)后來紅山文化的聚落形態(tài)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使其在遼西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文化發(fā)展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過渡作用。
興隆洼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被認(rèn)為是遼西地區(qū)目前已確認(rèn)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6],經(jīng)發(fā)掘的聚落有白音長汗遺址一期、查海遺址一期和楊家洼遺址,其中有13處為單純的小河西文化遺存,包括1座中型聚落、5處小型聚落和7個(gè)最小聚落;聚落為氏族聚居,一般有兩個(gè)等級(jí)的社會(huì)組織――小型房址為家庭,成排分布的中型房址為大家庭,如白音長汗遺址一期的3座房址中,F(xiàn)42面積最大,依次為F64,面積最小的是F65,可能為一個(gè)由家庭和大家庭組成的二級(jí)社會(huì)組織;查海遺址一期聚落的兩排房址則可能是一個(gè)由家庭、大家庭和氏族組成的三級(jí)社會(huì)組織[7]。
大量考古學(xué)材料表明遼西地區(qū)古文化遺存中從房屋因素的出現(xiàn)到聚落形態(tài)的形成,尤其是自興隆洼文化起環(huán)壕聚落的出現(xiàn)對(duì)后來“城”的概念的出現(xiàn)具有重要意義。
三、宗教祭祀
尹弘兵先生曾提到,文明起源有四個(gè)層次,其中第四個(gè)層次便是宗教的力量[8]。他指出某些學(xué)者所強(qiáng)調(diào)的“視禮制為進(jìn)入文明時(shí)代的重要標(biāo)志,認(rèn)為禮制對(duì)中國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義”這一觀點(diǎn),其實(shí)是沒有理清禮制與宗教關(guān)系。他認(rèn)為禮制本身也是宗教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在西周以前并無明確劃分,其后禮制才從宗教中獨(dú)立出來。那么,在政教合一的史前社會(huì)和夏商時(shí)期,宗教祭祀活動(dòng)的實(shí)質(zhì)更傾向于一種極為重要的政治活動(dòng),而在這一過程中所用到的禮器,就成為國家權(quán)力的象征。
遼西地區(qū)古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小河西文化,在興隆洼文化時(shí)期發(fā)展成一種習(xí)俗,白音長汗F19出土的石雕人像是該文化時(shí)期崇祖觀念形成的重要實(shí)證,F(xiàn)19的性質(zhì)也因此發(fā)生了變化,兼具居住和祭祀功能。這種對(duì)于祖先的崇拜行為到了趙寶溝文化時(shí)期在內(nèi)涵上得到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由以小山遺址出土的人首石越為代表,鉞是祭祀活動(dòng)中的重器,而鉞首刻畫的人首形象則應(yīng)是“祖”的形象,不難推測(cè)這應(yīng)是為祭祀專門刻畫制作的。紅山先民為承蒙祖先庇佑而進(jìn)行的祭祀活動(dòng),在這一時(shí)期更加繁榮,西水泉遺址、東嘴山遺址和牛河梁女神廟等遺址出土的女性雕像[9]更具濃厚的崇祖思想。另外,對(duì)于動(dòng)物和天地的崇拜也都不難在這一地區(qū)的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中發(fā)現(xiàn)――對(duì)于龍的崇拜,早在興隆洼文化時(shí)期就已處于孕育期,到趙寶溝文化時(shí)期開始形成為習(xí)俗,到了紅山文化時(shí)期,龍崇拜邁入成熟階段并對(duì)后世逐漸形成的龍文化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而對(duì)天地的崇拜則是紅山文化時(shí)期原始和祭祀體系發(fā)展到一定高度的另一重要體現(xiàn),修建在牛河梁遺址、東嘴山遺址和草帽山遺址的祭壇和積石冢體現(xiàn)了天圓地方觀念的成熟,更有大家指出這種大型禮制建筑性質(zhì)的壇、廟、冢表明早在3000BC前我國就已出現(xiàn)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駕其上的更高級(jí)別的社會(huì)組織形式[10]。
這樣看來,古代的祭祀本質(zhì)上就是人神之間的對(duì)話,而最初的等級(jí)差別也產(chǎn)生于人神之間,后來那些主持祭祀活動(dòng)、溝通神靈的巫祝們的等級(jí)地位也隨之逐漸高于眾人,由此出現(xiàn)了高低貴賤的社會(huì)等級(jí)差別,不同等級(jí)之間的人進(jìn)行交往時(shí)要遵循特定的儀式,既禮。“國家”就是這種等級(jí)差別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產(chǎn)物。實(shí)際上,若溯其根源,這種成形于三代的古禮,應(yīng)與遼西地區(qū)以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史前禮制有著某些淵源關(guān)系。
四、結(jié)語
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徑,從居住形態(tài)上講,是從自然村落發(fā)展到都城;從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上講,是由部落發(fā)展到國家;從意識(shí)形態(tài)的發(fā)展上講,是由對(duì)神靈的單純崇拜發(fā)展到獨(dú)具規(guī)模和形制化的祭祀活動(dòng)。遼西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各文化遺存正是從上述三個(gè)方面對(duì)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到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與其他古文化區(qū)共同使中國史前文明發(fā)展成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jié)構(gòu)[11],成為中國文明起源多中心論的一例有理證據(jù)。
參考文獻(xiàn):
[1]田廣林,劉特特.中國文明起源的遼西個(gè)案觀察[J].遼寧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3).
[2]王小青.中國粟作農(nóng)業(yè)起源研究綜述[J].黑龍江史志,2013(21).
[3]席永杰,滕海鍵.興隆洼文化研究綜論[J].赤峰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2).
[4]席永杰,滕海鍵.興隆洼文化研究綜論[J].赤峰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2).
[5]趙賓福.關(guān)于趙寶溝文化的聚落形態(tài)問題[J].華夏考古,2008(3).
[6]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論[J]考古文物,2005(1).
[7]索秀芬,李少兵.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態(tài)[J].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2008(1).
[8]尹弘兵.關(guān)于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問題[J].社會(huì)科學(xué),2007(4).
[9]徐子峰.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辨析[J].松州學(xué)刊,2010(5).
篇4
一、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形制分類
根據(jù)形制差異,我們將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分為三類:
第一類 正面像,頭戴冠,梭形眼,蒜頭鼻,一般耳下部飾環(huán)。這類玉雕像又可以分為三種造型:
A型 上下獠牙外露,頭部有角,帶有平冠,耳下部的環(huán)內(nèi)穿孔(見圖1)。
根據(jù)已的考古資料,這種造型僅見于肖家屋脊遺址甕棺葬W6∶32,雕像布滿白色土沁,整體為三棱形,正面前凸。嘴部上下伸出獠牙,頭部飾有彎角為其最大特點(diǎn),顯然是人與獸的結(jié)合體。石家河遺址2015年發(fā)掘的主要收獲中也出現(xiàn)有這種造型的玉雕像,與肖家屋脊遺址甕棺葬W6∶32的造型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是新發(fā)現(xiàn)的這件尖角造型復(fù)雜,向兩邊伸出,平冠的兩邊也變窄出角。
B型 無獠牙和角,帶有平冠,近似于常人(見圖2)。
大部分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像都屬于這一型,總計(jì)13件。包括石家河遺址出土的1件,肖家屋脊遺址甕棺葬W6∶14和W6∶41的2件以及羅家柏嶺遺址除T20③B∶16外的T20③B∶1、T20③B∶3、T20③B∶18、T27③B∶1和T7①∶5等10件為代表。
C型 無獠牙和角,所戴冠的帽檐下彎(見圖3)。
荊州棗林崗遺址WM4∶1、鐘祥六合遺址W18∶1和石家河遺址W9新出的1件玉雕像為代表。
第二類 浮雕于玉管表面,梭形眼,蒜頭鼻,頭部造像形似頭發(fā)盤成圈狀在腦后挽成發(fā)結(jié)或系于頭部的裝飾品(見圖4)。
肖家屋脊遺址甕棺葬W7∶4和石家河遺址甕棺葬W8中新出的1件為代表。
第三類 為側(cè)面人頭像,梭形眼,蒜頭鼻,頭部有冠。
A型 有一首側(cè)面人頭像,以肖家屋脊W6∶17和羅家柏嶺T20③B∶16為代表(見圖5)。
B型 連體雙首玉雕人像(見圖6)。
石家河遺址2015年發(fā)掘的主要收獲中W9出土的連體雙首玉雕人像為代表。
此外還見一類僅有眼睛沒有其他五官的造像,張緒球先生將其定名為“抽象人頭像”,亦歸入玉雕人像之列[17],以肖家屋脊W6∶38(見圖7)、W6∶9為代表。但由石家河文化諸多玉雕造型來看,其為人面像的可能性不大,推測(cè)應(yīng)為動(dòng)物或其他造型。因?yàn)槌鐾寥嗣嫦竦难劬Χ紴樗笮窝郏@些抽象造型僅有兩個(gè)左右對(duì)稱的眼窩,俱為圓形。石家河文化和棗林崗遺址發(fā)現(xiàn)的虎頭像多為圓形眼(見圖8),和此類雕像有相似之處。尤其是W6∶9造型更像是眼下部雕刻一長喙,接近于鳥形。同時(shí)玉雕像一般為片狀和弧凸?fàn)睿ぜ椅菁筗6∶38、W6∶9橫切面為多邊形的造型。綜合這幾個(gè)方面的差異,故將肖家屋脊W6∶38、W6∶9類玉雕像排除在玉雕人像之外。
二、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與其他玉器文化玉雕像的聯(lián)系
作為長江中游新石器時(shí)代末期考古學(xué)文化的代表,石家河文化早期遺存是在屈家?guī)X文化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但在已發(fā)現(xiàn)的屈家?guī)X遺址中,并未發(fā)現(xiàn)有玉雕人像出土。由于石家河文化玉器多發(fā)現(xiàn)于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而石家河文化晚期與早期在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溯源問題較為復(fù)雜,有待更多考古資料的出土。
石家河文化大抵與龍山文化同時(shí),關(guān)于一類A型玉雕人像的來源,杜金鵬先生認(rèn)為“受到大汶口文化影響的石家河文化,產(chǎn)生出山東龍山文化類似的神`形象,當(dāng)不無可能”[20],并提出一類A型玉雕人像也可能“原本就是龍山文化之物”[21]。但是從已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山東龍山文化的玉雕人像并不多見,杜金鵬等先生得出上述結(jié)論的一個(gè)重要依據(jù)是臨朐縣西朱封遺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其兩側(cè)有堆成的六個(gè)彎角,與一類A型玉雕人像的彎角造型大體一致。張緒球先生也提出“石家河文化中帶獠牙的人面像、鷹和透雕的抽象虎頭像,在山東龍山文化中都有發(fā)現(xiàn)。……石家河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玉器都擅長用減地陽文和透雕方法。……因此,石家河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玉器在淵源關(guān)系上,應(yīng)是前者接受后者的傳播”[22]。 已有的考古資料中一類A型玉雕人像僅發(fā)現(xiàn)兩件,除一類A型外石家河文化其他造型的玉雕人像在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中都未有發(fā)現(xiàn),所以石家河文化玉器與山東龍山文化玉器應(yīng)有一定的交流,但是石家河文化玉雕像是否在山東龍山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影響下產(chǎn)生的還有待考證。
就遼河流域而言,紅山文化尚未發(fā)現(xiàn)與石家河文化相似的玉雕人像作品。紅山文化牛梁河遺址女神廟曾出土有一件面涂紅彩的泥塑女神頭像[23],女神的造型較為具象,與今人無異,這與石家河文化玉雕的造型差距較大。不過女神頭部也有形似平冠的造型,這可能是一種身份與地位的象征,與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冠飾作用相似,體現(xiàn)出新石器時(shí)代人們觀念上的共性。就長江流域而言,良渚文化的神面紋玉飾自成系統(tǒng),神人與獸面的搭配較為獨(dú)特,在玉器上多為陰刻,與一類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在造型上難以找到共同點(diǎn)。凌家灘玉器的整體形象與石家河文化差異也較大,以含山縣凌家灘遺址比較有代表性的M29出土的玉雕人像來看,其有人物的整體形象,頭部有冠、蒜頭鼻,眼眉刻畫層次不清,大嘴微閉,雙手置于胸前,膝蓋彎曲,似呈蹲踞狀[24]。這與石家河文化僅做出玉雕人像的頭部和多用片雕等的造型也完全不同。綜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受到上述三者文化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上文中提到一類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應(yīng)該是人與獸的結(jié)合體,是上下獠牙外露、頭部有角的一類B型的變形,可能是一類B型和獸面形象相結(jié)合而成的,這種推測(cè)在石家河文化玉器內(nèi)部就可以找到根據(jù)。湖北鐘祥六合遺址W6∶1(見圖9)、肖家屋脊遺址W6∶15與肖家屋脊遺址W6∶60(見圖10)一般認(rèn)為是虎頭像,但我們看石家河玉虎頭(見圖8)的耳尖處上翹都不明顯,而且眼睛圓鼓,是相對(duì)寫實(shí)化的動(dòng)物形象。而湖北鐘祥六合遺址W6∶1、肖家屋脊遺址W6∶15與肖家屋脊遺址W6∶60的獸頭耳部都明顯上翹,眼睛為梭形。所以從整體造型來看,將這三件玉雕定為玉獸頭更為準(zhǔn)確。將一類B型玉雕人像與這些獸面形象結(jié)合就是一類A型的造型,所以一類B型玉雕人像在周邊文化中找不到較多影響關(guān)系時(shí),獸面形象則在許多新石器文化中都有發(fā)現(xiàn),找到與石家河文化玉獸面相似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的獸面造型可能是探索石家河玉雕像相關(guān)問題的又一個(gè)思路。山西襄汾陶寺墓地M22出土的獸面形玉飾頭上有三凸冠,同時(shí)有一對(duì)對(duì)稱的彎角,雙眼近似梭形[25],這與湖北鐘祥六合遺址W6∶1玉獸面的造型幾近一致。而就陶寺獸面形玉飾的整體造型來看,比臨朐西朱封遺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更接近于一類型石家河玉人雕像的造型。當(dāng)然陶寺墓地M22出土的獸面形玉飾也可能是石家河文化向西北傳播的產(chǎn)物,即便是這樣,也表明陶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玉器存在有交流。
由上述的分析來看,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應(yīng)該與山東龍山文化、陶寺文化關(guān)系密切,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玉雕人像則與石家河文化的差異較大,對(duì)其影響較小。
三、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證
新石器時(shí)代起,玉器就被先民賦予了通天禮神的靈性,并被認(rèn)為能夠保護(hù)人的肉體和靈魂,因此產(chǎn)生了以玉殮葬的習(xí)俗。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與其他玉器一樣,應(yīng)該也具有一定的原始的因素。具體來說,不同造型、不同發(fā)現(xiàn)地點(diǎn)和數(shù)量中應(yīng)還包含有豐厚的文化內(nèi)涵在其中。
關(guān)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證,楊建芳先生認(rèn)為:“這種神像并非某一地區(qū)個(gè)別小人物的造型,而應(yīng)是石家河文化居民及其后裔長期共同信奉的神o或祖先崇拜的偶像。其性質(zhì)與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相似。”[28] 鄧淑萍先生認(rèn)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29],“神祖”的形象取自于現(xiàn)實(shí)中的人,加上一些表示神靈的符號(hào)如獠牙、鳥羽等。從一類A型玉雕人像上下獠牙外露、頭部有角、帶有平冠等特征來看,確實(shí)不同于一般的人類,是一種神化的人的形象。所以楊、鄧兩位先生的觀點(diǎn)就一類A型玉雕人像的身份解讀來說是可信的。但一類B型與一類C型玉雕人像無獠牙和角,所戴冠為平冠或帽檐下彎,二類與三類的玉雕人物形象也相對(duì)平實(shí),接近于常人形象,所以將這四類人像與一類A型的身份都作為神人形象似有不妥。要考證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還要提前解決一個(gè)問題:為什么玉雕人像被人為地做成了幾種不同的造型,而且每種造型的數(shù)量比例差距較大?其中一類B型13件,一類A型2件,一類C型3件,二類2件,三類A型2件,三類B型1件。由于相關(guān)石家河文化的遺址還在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中,即使考慮到考古資料的不均衡性,由表1中的數(shù)據(jù)可以明顯看出一類B型是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主流,且在肖家屋脊遺址、石家河遺址、羅家柏嶺遺址三處主要的石家河文化遺址中都有發(fā)現(xiàn),而其他的幾種類型相對(duì)較少。結(jié)合以前學(xué)者們的研究成果和這種數(shù)量的較大差異,很容易得出一個(gè)結(jié)論:一類B型玉雕人像身份即使低于一類A型玉雕的神人地位,但在石家河文化中有著很高并相對(duì)特別地位,而一類C型、二類、三類A型和三類B型這幾種的地位可能是低于一類的A型和B型的,處于附屬地位。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一類B型玉雕人像是一種類似于常人的形象,出土數(shù)量最多。最重要的一點(diǎn)是這種人像僅發(fā)現(xiàn)于石家河文化遺址,是一種獨(dú)有的造像。在一類A型玉雕人像是神人形象的基礎(chǔ)上,一類B型玉雕人像的身份可能與之不同。推而廣之,一類C型、二類、三類A型和三類B型被做成各種造型應(yīng)該也不能簡單地像鄧淑萍先生認(rèn)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那么簡單。不同的造像可能具有不同的人物身份,代表著不同的社會(huì)階層。一類A型玉雕人像是一種石家河先民想象的神的形象,是一種自然的神o,是可以保佑部族不受侵害的神靈。而一類B型玉雕人像則更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祖先或者首領(lǐng)形象的造型,在其部族的內(nèi)部擁有相對(duì)較大的權(quán)力。其他的各類形象則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的其他A層的造型,相對(duì)于一類A型與一類B型玉雕人像,他們的地位較低。但不同造型也有著嚴(yán)格的等級(jí)劃分,類似于印度的種姓制度,社會(huì)群體被分作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個(gè)階層。
具體來看,第三類的玉雕人像都為側(cè)面、戴尖冠或高冠甚至雙首的形象,背后應(yīng)該也有一定的寓意。由于其身份地位低于一類A型與一類B型玉雕人像,一類A型為神靈的象征,一類B型掌握著類似于王權(quán)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結(jié)合第三類較為奇特的外形和部分具有雙首的形象,推測(cè)其最有可能是具有通神之能的巫師形象。第二類的形象中,頭部沒有冠的造型,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新石器時(shí)代冠已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故推測(cè)第二類現(xiàn)發(fā)現(xiàn)的3件玉雕的地位在所有玉雕人像中最低。
綜上所述,我們推測(cè)出的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級(jí)排列大體是:第一類最高,是神人和掌握著統(tǒng)治權(quán)即王權(quán)的人;第三類為巫師的造型,是具有通神職能的人;第二類則相對(duì)較低,接近于平民。這種推測(cè)可以從玉雕人像的出土墓葬和隨葬品中得到佐證。邰鑫成先生通過整理所屬石家河文化的多座墓葬,分析其墓制大小和隨葬品的多少提出“石家河文化社會(huì)分為四個(gè)級(jí)別”[30]:一級(jí)為統(tǒng)治階層,有指揮、統(tǒng)治民眾的權(quán)力;二級(jí)有一定的社會(huì)地位和有限財(cái)富,為中間階層;三級(jí)為有的少量社會(huì)財(cái)富,社會(huì)地位不高,是社會(huì)的中下階層;四級(jí)為社會(huì)最為低下的赤貧階層。石家河文化社會(huì)已形成了一個(gè)從高到低的金字塔狀社會(huì)。邰鑫成先生的觀點(diǎn)與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級(jí)排列是大體一致的,印證了石家河文化的等級(jí)制度可能就是產(chǎn)生不同玉雕神像的根本原因,也就解釋了各種玉雕人像的出現(xiàn)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階層的反映,其數(shù)量與等級(jí)高低有一定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玉雕人像發(fā)現(xiàn)數(shù)量較少,文章并未對(duì)其進(jìn)行歷時(shí)性的分析,隨著考古發(fā)現(xiàn)的增多,將來或可對(duì)此另文探討。
注釋:
[1]a.湖北省文管會(huì).湖北京山、天門考古發(fā)掘簡報(bào)[J].考古通訊,1956(3).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遺址2015年發(fā)掘的主要收獲[J].江漢考古,2016(1).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shí)代遺址[J].考古學(xué)報(bào),1994(2).
[3]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石家河考古隊(duì).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4]荊州博物館.棗林崗與堆金臺(tái)[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99.
[5]荊州地區(qū)博物館,鐘祥縣博物館.鐘祥六合遺址[J].江漢考古,1987(2).
[6]杜金鵬.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淺說[J].江漢考古,1993(3).
[7]周光林.淺議石家河文化雕塑人像[J].江漢考古,1996(1).
[8]葉舒憲.石家河新出土雙人首玉i的神話學(xué)辨識(shí)《山海經(jīng)》“珥蛇”說的考古新證[J].民族藝術(shù),2016(5).
[9]張緒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J].江漢考古,1992(1).
[10]劉德銀.石家河文化的玉器[J].收藏家,2000(5).
[11]郭立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Y棺葬研究[J].四川文物,2005(3).
[12][16]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石家河考古隊(duì).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16.
[13]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7.
[14]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5.
[15]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9.
[17]張緒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概述[J].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
[18]湖北省荊州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石家河考古隊(duì).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18.
[19]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3.
[20]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4.
[21]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9.
[22]張緒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概述[J].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9.
[23]孫守道,郭大順.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J].文物,1986年8).
[24]古方.中國古玉圖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1.
[25]古方.中國古玉圖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68.
[26]荊州地區(qū)博物館,鐘祥縣博物館.鐘祥六合遺址[J].江漢考古,1987(2).
[27]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石家河考古隊(duì).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27.
[28]楊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淵源探索――兼論有關(guān)新石器時(shí)代文化傳播、影響的研究方法[J].南方民族考古,1987(1).
[29]鄧淑萍.再論神祖面紋玉器[J].東南玉器,1998(1):56.
[30]邰鑫成.石家河文化墓地研究,(碩士學(xué)位論文),吉林大學(xué)文學(xué)院,2004.46.
作者單位;
劉亭亭 國家文物進(jìn)出境審核海南管理處
篇5
關(guān)鍵詞: 考古 文化 遺產(chǎn) 保護(hù) 發(fā)現(xiàn) 發(fā)掘 研究 開發(fā) 利用
考古學(xué)是“根據(jù)古代人類活動(dòng)遺留下來的實(shí)物史料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學(xué)科。歷史科學(xué)的一個(gè)部門。實(shí)物史料即各種遺跡和遺物,大多數(shù)埋藏在地下,考古工作者通過發(fā)掘發(fā)現(xiàn)它們,進(jìn)行研究,闡明古代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狀況和物質(zhì)文化面貌,進(jìn)而探討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對(duì)于復(fù)原沒有文字記載的原始社會(huì)和少數(shù)民族古代歷史,考古學(xué)有其特殊的作用。”[1]
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具有十分重要的保護(hù)作用,而這種保護(hù)作用又具體體現(xiàn)在許多層面,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層面,我們分別進(jìn)行論述。
一、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作用
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作用,首先體現(xiàn)在它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作用上。因?yàn)榘l(fā)現(xiàn)發(fā)掘是基礎(chǔ)與前提,只有先發(fā)現(xiàn)發(fā)掘,然后才談得上保護(hù)。如果沒有發(fā)現(xiàn)發(fā)掘,保護(hù)又從何而來呢?
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作用在發(fā)現(xiàn)發(fā)掘作用體現(xiàn)的實(shí)例,不勝枚舉。例如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fā)現(xiàn)發(fā)掘的仰韶文化遺址,就成為我國新石器時(shí)代的文化遺址之一,因該遺址遺物中有彩陶,故又稱“彩陶文化”遺址。又如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龍骨山洞穴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北京猿人化石,經(jīng)古地磁法測(cè)定,其絕對(duì)年齡為距今約70—23萬年,地質(zhì)時(shí)代屬于更新世中期。至今共發(fā)現(xiàn)40余個(gè)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個(gè)體。
由此可見,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是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作用的基礎(chǔ)與前提。
二、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研究作用
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只是第一步,而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核心與關(guān)鍵,是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研究。
首先是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其中主要是對(duì)文化遺址與文化遺物的保護(hù)。例如仰韶文化遺址——河南澠池仰韶村,就被確定為國家重點(diǎn)文物保護(hù)單位。
同時(shí)是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其中主要是文化遺物——文物的系統(tǒng)化、科學(xué)化研究。例如殷墟,位于河南安陽小屯村及其周圍,為商代后期都城遺址,商代自盤庚到帝辛(紂)在此建都共達(dá)273年,是我國歷史上可以肯定確切位置的第一個(gè)都城,也是全國重點(diǎn)文化保護(hù)單位。而在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生產(chǎn)工具、生活用具、禮樂器、甲骨等,有關(guān)專家都進(jìn)行了系統(tǒng)化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甲骨刻辭,早在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在此首次發(fā)現(xiàn),后于1928年開始考古發(fā)掘,先后出土多達(dá)10萬余片,上面的甲骨文為我國最早的文字,已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單字共計(jì)4500字左右,已認(rèn)識(shí)的有1700字。歷代專家學(xué)者對(duì)甲骨文進(jìn)行了全面系統(tǒng)、科學(xué)細(xì)致的研究,并形成了專門的學(xué)科——甲骨學(xué),包括甲骨文歷史、甲骨文流傳、著錄、卜辭內(nèi)容研究、龜甲獸骨種屬等。其中重要著述有孫詒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考釋》等。又如1972—1974年先后兩次發(fā)掘的湖南長沙東效馬王堆漢墓,對(duì)其文化遺物印章、印泥、套棺、木炭、白膏泥、男尸枯骨、帛書、帛畫、彩繪、絲織品、樂器、漆器、完整女尸、竹筒等,也進(jìn)行了全面系統(tǒng)、深入細(xì)致的研究。證明這些文物,為研究西漢初期的歷史與當(dāng)時(shí)手工業(yè)生產(chǎn)、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可靠的實(shí)物資料。
當(dāng)然,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研究,除國家的高度重視、大力支持以外,還與國力的強(qiáng)弱弱有關(guān)。例如北京猿人化石共40余個(gè),但在1941年大部分落入美國人手中,至今不知去向。而建國后發(fā)現(xiàn)發(fā)掘的文化遺跡與遺物,則絕大多數(shù)都得到了完好的保護(hù)。
三、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開發(fā)利用
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并不是消極封閉、被動(dòng)靜止的,而是消極開放、主動(dòng)動(dòng)態(tài)的。其中的重要之點(diǎn),就是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開發(fā)利用。
這方面成功的例證很多。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系著名的明清宮廷建筑與宮廷史跡,也是古代藝術(shù)博物館,珍藏歷代藝術(shù)品和明清歷史文物多達(dá)100多萬件。現(xiàn)在已對(duì)外開放,供游人觀賞。又如1978年出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編鐘,經(jīng)考古專家與音樂專家合作,對(duì)全套曾侯乙墓編鐘音樂進(jìn)行了全面研究,并進(jìn)行了復(fù)制。由湖北博物館、湖北藝術(shù)學(xué)院組成編鐘樂團(tuán),并和中國廣播藝術(shù)團(tuán)民族樂團(tuán)、交響樂團(tuán)合作,于1984年建國35周年在北京聯(lián)合舉辦了曾侯乙編鐘音樂會(huì),演奏了《楚商》、《春江花月夜》、《秦王破陳禾》、《滿江紅》等曲目,取得了很好的藝術(shù)效果。“向當(dāng)代觀眾展現(xiàn)了2400年前的編鐘等古樂器的風(fēng)采。”[2]
參考文獻(xiàn):